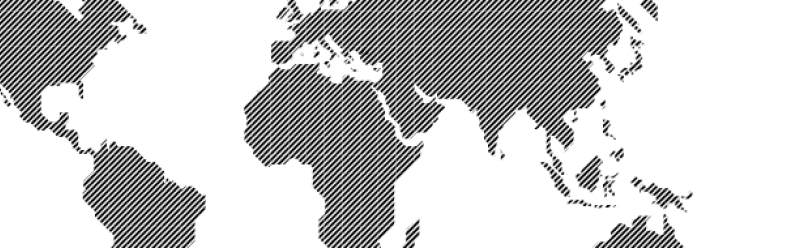第十一章
左翼中国文献简介
这里主要涉及了中国文学界推崇的西方左翼作家。
问题:西方左翼作家对中国资本主义化变革后是怎么看的?
论点:左翼作家始终在用他们理想化的,国家财富、国家与民众之间成功合作关系来衡量资本 主义改造。这导致对事实的错误判断。而早期的中国使现在的一些人对革命还抱有希望,对中 国重新诠释是必要的。
关键词:德国左翼、Hyekung Cho、何清涟Qinglian He、 Theodor Bergmann、Helmut Peters、Giovanni Arrighi、 Joachim Bischoff、德国工会组织在中国
当代中国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了吗?还是--与乍看上去不一样--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今天甚或已经成为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对国际力量关系产生好的影响的一种替代性力量?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吗?它会更多考虑人民吗?还是可以并且必须指望中国工人奋起造反?
左派讨论和著作中偏爱关注此类问题。给定的答案都是主观猜测与评价,这一点是事先就决定了的,但却无所谓,因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想讨论的是这个发生了巨变的亚洲大国是否承载着希望--无论以何种方式。
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如此。当时,中国共产主义的左派友人们在意的是借助这个国家事实上取得的成功赢得西方群众,从根本上来说,他们误以为自己原本就与西方群众心心相印。一场真正的革命和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大国应当帮助本国的昏厥,人们于是便对人民共和国产生了想象。鲜有人在乎对毛泽东主义这种变化形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解释并从中得出某些结论,相反,人们将一切奉为寓言,他们谈论着人民公社与工厂取得的不断胜利,文化大革命则被说成是扣人心弦的民主基层运动......
不管怎样,这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为了加速当时左派崛起的成功。这个时期的“运动”现在所剩无已,但有一样东西似乎生命力颇为顽强:那便是折射出涉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或好或坏的条件的需求--尽管(或许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事业已经相当罕见了。无论如何,这里的左派在讨论中国的“形势”时,(仍然)喜欢让人感觉这是一个重要的实践[1]--无论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政治局,还是广州罢工者的集会。
在此,可以区分三大潮流:第一种是认为中国政治面临艰巨任务的批评--无论人们对此有何具体看法--,认为中国政治很难完成这些任务。无论是寄希望于执政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从长期看有能力实现“必要的改革”,还是认为中国统治阶级腐败透顶,沉醉于权力且难以理喻,因此唯有取代他们才能有所帮助,归根结底,这是从同样的良政理想主义中得出的两种可能的结论。第二个潮流是认为中国仍是社会主义政权的观点,或者至少当政的是正在形成中的替代性世界政治。第三则是希望这个亚洲国家现在已经是或者即将成为社会抵抗的中心。以下仅介绍上述立场的某些有代表性的人物。
许多左派人士对人民共和国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人民共和国出卖了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但首先是出卖了社会主义思想。这经常表现在对毛泽东中国存在的大量有趣和错误的观点--本书第一部分试图对该问题予以纠正。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允许国内存在贫困与不平等的中国政府的失望同时也表明这些人坚信本应有良政。良政应当尽可能同时完成“现代化”--很少有人会想到重返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并且避免中国一切令人不快的东西:社会阶级的出现,腐败环境遭到破坏和国家的压迫。在此,经济转轨的目标--国家开始实行西方利润生产体制,这种“原始积累”从任何方面看都是一种暴力行为--根本没有被真正注意到。相反,人们对其进行了颇具善意的抽象(“现代化”,“发展”,“改革”),并由此对所有看似根本不必要的条件与作用进行了批评。因此,这种维模式从根本上说非常简单,广为传播并且在我们国家广为人知:人们将想象中的良好意愿或者真正的成功与没有人希望看到的坏的结果区分开来。区别在于下述评价,即是否认为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人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还是认为这些人不可理喻。
Hyekyung
Cho写的“中国通往资本主义的长征”一书信息量很大,她以丰富的见解研究了许多具体问题(财政政策,入世,中央政府与地区与各省的关系)。归纳起来说,她对人民共和国取得的“增长和工业发展”给予了赞扬,而对其社会问题进行了批评,她认为“繁荣的出口经济(...)的灿烂前景与进一步加剧了贫富鸿沟的就业危机的黯淡前景相伴”(2005年,第286页及下)。因此,她是根据“好的方面,坏的方面”的口号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批评。这两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它们又如何构成一个整体,尚存的与财富相比在继续扩大的贫困在市场经济中是致富的手段,这一切她并没有注意到--或许是由于她认为中国“发展”以及在世界上后发崛起的目标无可指摘。
2006年,何清涟对自己的国家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现代化陷阱中的中国”。她在此书中对没收中国的全民财产进行了抨击,还抨击了房地产投机商的不当致富,腐败以及非法经济活动--由此肯定说出了许多中国爱国者/共产党人的心里话。她举了大量实例,记录了中国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借用马克思的概念将其归纳为“原始积累”。马克思这个概念指的是第一个“原始”没收所有人的生存手段及攫取货币财富的阶段,通过让整个社会服从资本积累的原则,这一切便相应地继续下去了。何清涟则将这两个不可分割的现象分离开来,一方面,她认为上述伴随着现实社会主义社会通往资本主义的特殊道路的原始积累现象是不必要的弊端,谴责执政的共产党人未能取得成功,但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积累视作中国社会主义重要而且必要的继续:“改革(...
...)借鉴了‘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以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成功经验,对外国采取了谦虚开放的态度,以显示它愿意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2006年,第32页)。因此,她接下来便进行了区分,一方面是她在美国和欧洲发现的干净的并“合乎伦理的”利润生产,另一方面则是她的祖国实行的疯狂和没有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自1989年起得到政府同意,自彻底拒绝一切政治改革之后便开始了。她不想得出个人致富是其共同的根本原则这一结论。
这位女作者对自己国家的政治阶级则不存任何幻想。她不相信“倾向于腐败”的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人会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必要的调节。同样,她对中国人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由于数千年的皇权统治和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人民已经没有了任何自由意志,它只是坐等统治者变好,坐等统治者对自己公允一些。因此,何清涟这本书在中国包括共产党内部得到了一定赞同后又被禁止,现在她希望西方国家能够承认此书也就不足为奇了。她或许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及它们在政治上对待人民的方式是正确的,中国的福音应来自这里。因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跳出自己的阴影,出版了一本其立场与自己通常并不支持的德国左翼党的观点相差无几的书也同样不足为奇。作为针对自己不喜欢的国家的证人,就连左派也是可以利用的...
...
1990年以来,“左派”必须接受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无可争议的胜利这一事实。在无望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中找到自己可以归依以及至少可以从思想上相通的与上述世界抗衡的大国的力量与思路的需要创造出了分殊艺术,人们可以借此看起来与“主流”有所区别。中国“发生了变化”,这是一回事--肯定也有许多在左派作家看来必须予以拒绝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个亚洲大国的确从某种程度上对美国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单极世界秩序”提出了质疑,美国并非毫无保留地为中国的成功感到高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此相比,可以忽略美国的干扰和(有条件的)对抗恰恰是由于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并且越来越崛起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点:中国“已经以某种方式”成为替代性世界秩序大国--这一点谁能否认呢?
Theodor Bergmann写的
(“21世纪的红色中国”,2004年)一书将这种相对的立场推向了极端。他认为:“中国正由一个发展中大国迈向社会主义”(前言)。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是并且以后也会承载着所有正派左翼人士的希望,他径直把中国改革派及其看待事物的意识形态观点拿了过来。值得庆幸的是,在经历了毛泽东那些蔑视政治经济学客观规律并且让人民不堪重负的唯意志论的运动之后,改革派终于打破了“计划与市场相互排斥这一(引文出处同上,第14页)伪(!)马克思主义(!)的禁忌(!)”,终结了“不再必须的”与世界市场的脱钩。由于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不同,它自己并没有退出,而是继续公开承认社会主义及其最终目标,因此,一个真正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忠实原则又狂妄自大--终于高兴地看到总算有一个真正成功的国家站在自己一边。
Helmut
Peters(“寻找浅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世纪走向社会主义”,2009年)尽管至少从形式上理解了计划与市场一定程度上互相矛盾,并且鉴于相关后果(“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一切都(成为)商品”,“残酷的竞争”,“社会分化”,引文出处同上,第412页),他对中国同志的路线表示了批评性的保留。不过,对于一个从根本上来说同中世纪一样落后的国家来说,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是值得称赞的进步,这种思想对他极具吸引力,以至于他漠视了许多事情,而这些事情作为上述生产力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结果引起了Peters的注意。此外,如果他喜欢中国的政策,便会将其解读为客观规律的结果,这些规律大多根本不可能允许与北京所做决定不同的东西,在这方面,他堪称大师。“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正常’条件下应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任务。如果它想在给定条件下完成上述任务,并由此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一般条件,它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资本以及它作为主要‘驱动中心’的推动力。”(引文出处同上,第26页)。共产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及其集团的规模完全不同--引进了西方技术与西方资本,在他看来,这同中国致力于崛起为“力量全面加强的世界大国的”努力一样都是必要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解释的国家利益,从替代性社会主义的正确性立场出发,这就是对的:“我认为调动全国力量加速让国家强大起来以在未来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保障国家安全与独立的取向是正确的。”(引文出处同上,第469页)。由于Peters从根本上与中国保持绝对一致,并且对中国声称自己仍然在发展社会主义这一点坚信不疑,他开始寻找个别人与个别干扰趋势中存在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副”作用的原因。与对其前任邓小平和后任胡锦涛不同,他认为江泽民政府具有新自由主义思想--这(总之比允许进行市场经济考量的原则性决定更)应对中国目前脆弱的工资关系与社会不平等负责。相反,他指出胡锦涛为首的现政府提出了诸如“以人为本”(引文出处同上,第510页)和“和谐社会”目标等最为抽象的措辞,正因为如此,将他们宣布为获得政治好感的人。中国现在的政治领导人管理的是此前改造进程的结果,他们又是如何对此进行管理以尽可能不受干扰地确保以对国家有利的方式继续该进程,这一点则是无所谓的。Peters蹩脚地看到了充满希望的远景:“现在的中国社会既非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它具有过渡特点。”(Peters,2008年,第26页)。这已说明了一切!
Giovanni Arrighi
(“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系谱学”,2008年)在真正全球设问的框架下对中国进行了观察。该设问是:某个国家为何崛起为资本主义领导大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来自巴尔的摩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Arrighi对各个历史阶段进行了一次有趣而值得一读的穿越,从资本主义第一个贸易中心热内亚,经过荷兰与英国,最后到达美国,他始终强调经济与武力成功之间的关联。他介绍了下述“规律”:在资本主义竞争关系下,能够对最大的国家积累进行监督的国家会领先--无论是建立自己工厂的形式,还是借助殖民地,再或者是通过全球资本出口。在此,军事力量被定位于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它反过来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自中国及其资本主义崛起参与进来之后,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潜力开始分离--因此,如果根据Arrighi的规律做进一步的想象,如果后起之秀能够将自己巨大的国家和人口众多的人民悉数变为资本主义积累的资源,它将取代美国。
除了这一思想,本书书名还展示了第二个思想:“亚当·斯密在北京”。Arrighi想拯救亚当·斯密的名誉,他认为斯密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希望将斯密视为价值理论家和国家理论家,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先驱。斯密--有时是“看不见的手”--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家维护秩序的这只手对于顺利运作的市场经济的决定性基本条件来说都是必不可缺的,其目的不应是让个人致富,而是让国家富裕起来(“国富论”是亚当·斯密主要著作的名字)。现在,两个论据结合在了一起:按Arrighi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亚当·斯密的建议,它不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而是由国家进行调节,并且始终关注国家这个更大的整体的利益,因此,他们才取得了成功。
在进行论证时,Arrighi在思想上让自己超越了所有进行全球竞争的国家。他既给那个力量正在削弱的必须重新实现工业化的世界领导大国出谋划策,也给应通过某些改革彰显自己雄心的正在崛起的中国人出主意。他的核心思想是:新自由主义正在经历失败--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对人民更有好处,而且经济上也更为成功。这听起来有点象是制度竞争的现代版本,老的社会主义者们眼前浮现出自己模范的国家政体。不管怎么说,Arrighi给反对全球化的人带来了一个内在的胜利: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通常将其看作理想主义者,他们全然不顾也不谈全球化竞争时代必须奉行国家的区位政策。现在,有位学者却向他们表明,一个廉洁的国家政权不仅能够更好地管理人民和环境的利益,而且也能在全球取得成功...
...
Joachim Bischoff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抑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7年)批评说,左派在讨论中国时要么满足于交流肤浅的陈词滥调(“残酷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要么就是不加批评地承认给这个国家加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语。两种做法他都反对,这是对的--但他提出的相反论据却是单薄的,他对中国转轨进程的研究自相矛盾,并且因为只是指出了许多现象而停留在表面上。对那些批评中国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Bischoff向其展现了中国的成功与成就--从世行都承认的“减少贫穷”,到“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增长率比印度高一倍!),直至成立的众多公司--,仿佛这一切必定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看起来,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他根本无法想象能够通过“另外的经济政策方式”消灭贫困--这是那些不通世故的左派应当牢记的!中国引入市场经济,这是件好事,中国对其“进行了社会主义调节”也是好事:“事实上,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权形式并存造就了整个再生产过程中更为开放的促进与发展。”(引文出处同上,第34页)另一方面:“无疑,政治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引文出处同上,第33页)。原因何在?为什么?Bischoff从哪里知道这一点呢?尽管他知道转向资本主义的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功与其“威权”政党之间的关联--归根结底,他赞扬的正是“社会主义的规制”,但在这个语境中,他很快便又忘记了这一点,为的是借助主流对中国的这项事业及其朋友提出指责,即由于中国在政治民主方面落在后面,因此才需要改进。其登峰造极的结尾是一个充分暴露了作者(完全是有意的?)不谙通事的小小愿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即20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应当为过渡到下一个发展阶段奠定经济社会基础。如果未来几年能够继续保持目前的积累速度,从事农业的人口就有望--类似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降至5%以下。
这样一来(?!),过剩经济就要把减少社会劳动时间和扩大社会文化服务提上议事日程。”(引文出处同上,第35页)。另一方面,Bischoff又固执地认为,无论中国情况怎样,“认为现有权力结构可以维系到那个时候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引文出处同上,第35页)。
与上述寄希望于中国领导层--无论是作为需要改革的资本主义大国还是已经可以让人寄予希望的替代性大国--的立场不同,许多左派人士寄希望于来自底层的社会反抗。在中国的经济特区,世界资本主义露出了丑陋的一面,国家规制对此全然不加制止,工人阶级象马克思恩格斯时代那样遭受着“绝对的”剥削,在穷困中悲惨地生活着,得不到任何法律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点儿什么”。工会会员要求增加工资或者减少劳动时间时,他们所在的厂领导会用中国式武器(将生产转移到远东地区)教育他们,他们希望中国工人能够组织起来进行反抗。与此相应,labournet和其它左派杂志都发表了文章,一方面描绘了中国工厂里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对各种形式的突发和有组织的反抗进行报道。但同以往一样,光有报道是不够的,有了这些,并不能将报道和采访中描述的对人的非人道待遇加以“细化”--因为得出正确的结论并非不言而喻的,而且那些中国人似乎也别想指望基督徒们会对他们表示同情。此外,光有这些也没有促使人们做些“什么”。如果从中国残酷的劳动条件中得出的结论是那里没有我们这里的工人通过艰苦斗争赢得的相应权利,那么工人运动的历史将再次得到丰富,即下述错误:国家干预应当让工资劳动关系变得可以忍受,而不是废除这种关系。
工会会员同企业领导一样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他们在经济特区工厂的残酷情况中看到的并不是中国和我们这里并无二致的经济目的,而首先是并不存在的东西:即他们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由社会福利国家进行调节的剥削和工会(参阅附件调研报道“中国的劳动世界”)。通过这种观察,他们(在国内,他们经常把持德国工会联合会及其政策)首先会对祖国德国实行的有秩序的人道的早期资本主义及其黑-红-金工会大加恭维。此外,他们希望中国新成立工会,以拯救本国急剧下降的关切。他们认为,中国工人采取相应的行动极为重要,十分必要,因为中国的倾销工资似乎让他们在德国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甚至让他们丢掉了饭碗。这种观点与结论一样引人注目,说到底,特别是德国工会近年来通过采取对本地需求负责任的工资政策以及政治上反对共产主义而对西方在冷战中大获全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胜利的结果--全球化资本对全世界加以利用--现在又反作用于他们,其形式是企业的敲诈,结果便是劳动条件持续恶化。现在,他们要求中国工人应当进行自己在本国不想并且似乎也不能够再进行的斗争。
[1] 目前,委内瑞拉查韦斯计划与此颇为相似,参阅相反的立场1/2007:“拉美向左转”--委内瑞拉在美国后院造反。
PDF-Dokument [184.7 KB]